上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博士,Uber,Airbnb,Bitcoin早期投資人Jeffrey Wernick做客巴比特直播間小喵有約,和大家聊了聊從比特幣到ICO到區塊鏈,普通投資人們到底存在著那些普遍誤區。
我為何選擇比特幣?
“我不信任貨幣體系,政府無需公民的同意,就可以無限增發紙幣,紙幣實際上就是一種IOU,我一直以來都是硬通貨的支持者。”
Jeffrey對硬通貨的興趣真正開始于1971年,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于黃金掛鉤。當時還是初中生的Jeffrey就敏銳的感覺到美元將會貶值,“那時我才15歲,就用積攢的5000美元買入了黃金股票。” 當年,年輕的Jeffrey在老師的推薦下讀了作家富蘭克林的書籍,他意識到“價值投資”是最終目標,5000美元殺入股市的他也沒有讓自己失望,僅僅3年時間,5000美元就增值上百倍,接近250000美元。
成功的投資眼光,讓Jeffrey在大學畢業之時,便已擁有1千萬美元的資產。年紀輕輕就實現了財富自由的Jeffrey是如何了解到比特幣,又是如何成為比特幣忠實的信仰者呢?
“我很早就接觸了電腦,學習了如何編碼。由于我數學也不賴,所以密碼學相關的我也都了解一些。”
1980年代,David Chaum密碼朋克教父級人物提出了“加密貨幣”的最初設想。1990年代,Jeffrey曾經嘗試創造自己的數字黃金,并向已經開展加密貨幣研究的Digicash(David Chaum創辦)展示商業計劃書,然而由于技術等各種原因,合作并未談成,Jeffrey只能打消了“數字黃金”的念頭。此后,Jeffrey依舊持續關注“加密貨幣”,“密碼學”相關信息,這也是為什么Jeffrey能在比特幣2009年誕生的第一年就積極參與了挖礦。
“當比特幣的創始區塊誕生的時候,我寫了篇文章,感到 ‘這一切真的就要發生了!’ ,在這之后,我就開始為比特幣生態做貢獻。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比特幣上投機,至今為止,我沒有賣過一個比特幣,從09年到現在,從1美元到1000美元到2萬美元,我見過太多的跌宕起伏,從1萬9美元跌到5,6千美元真不是什么大事。“
作為比特幣早期信仰者,Jeffrey不僅僅自己參與挖礦,還苦口婆心鼓勵身邊的朋友也參與進來。然而最開始并沒有什么人被說服,2011年-2012年間,才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朋友被說服入場。
“差不多是在25美元的時候,有一些朋友開始入場了,但是他們都很快就賣掉了。因為他們本質上不相信比特幣背后的哲學理念,都還是相信固有的法幣體系,所以我沒辦法說服他們法幣體系只是是場騙局,是非常脆弱的。但是,我08年叫他們做空股市的時候,實際上沒做空的,也是同一批人。我很多回報率高的投資,其實一開始都是沒有太多人認同的,就像我15歲時就買了黃金股票一樣。”
每當身邊的朋友都持謹慎態度,認為這是“愚蠢“的投資之時,Jeffrey反而會加大籌碼下注。 “黑天鵝“理論下的投資方式,讓Jeffrey在投資之路上賺得盆滿缽滿。對此,他表示訣竅其實很簡單:“大部分人猶豫時,我瘋狂。但我不貪婪,也從不恐慌,從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在被問到“為什么從未賣過一個比特幣”的問題時,Jeffrey表示道:“賣了就表示你認為法幣是優于加密貨幣的,那為什么要賣?”
為什么說大部分人都理解錯了加密貨幣?
比特幣是一種支付系統,這似乎已經是比特幣社區里的一種常識,畢竟中本聰在白皮書中就指出這是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然而,Jeffrey對此卻另有看法。
“為什么我說比特幣是一種價值儲存而不是支付工具呢?在現有階段下,法幣和比特幣共存,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人們會傾向于把良幣儲存起來,劣幣花出去,在現有情境下,比特幣即為良幣,法幣為劣幣。你相信加密貨幣,而不信任法幣,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又怎么可能會把加密貨幣花出去呢?”
在鑄幣時代,英國財政大臣格雷欣發現,當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鑄幣——“劣幣”進入流通領域之后,人們就傾向于將那些足值貨幣——“良幣”收藏起來。最后,實際價值較高的“良幣”漸漸為人們所貯存離開流通市場,使得實際價值較低的“劣幣”充斥市場。
這種現象不僅在鑄幣流通時代存在,在紙幣流通中也同樣存在。大家會把骯臟、破損的紙幣或者不方便存放的劣幣盡快花出去,而留下整齊、干凈的貨幣。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也比比皆是,而Jeffrey認為比特幣目前的情況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時候比特幣才可能用于支付呢?答案就是當你用完了劣幣的時候,才會開始使用好幣。當大部分人對法幣失去了信心,比特幣或者加密貨幣才可能真正被當作支付工具。
“全世界所有的錢,其中2/3用于存儲價值,1/3用于消費,用于支付。從存儲價值角度看,比特幣作為一個新的貨幣,它相對于法幣有非常大的優越性,因為比特幣的量是限定的,隨著我們創造價值越來越多,比特幣的價值會不斷的上升,它是非常優越的存儲價值年限,遠遠優于現在的法幣。”
我為何是個堅定的反ICO主義者?
ICO自出現以來,被眾多人吹捧為顛覆性的融資模式,被認為是去掉中間商的IPO。然而Jeffrey卻并不待見ICO,對于目前市值排名第二的以太坊,Jeffrey也認為還存在很大瓶頸。
“以太坊目前最大的應用還是ICO,繼加密貓之后,現在以太坊上最活躍的DAPP是FOMO3D,這是很搞笑的一件事兒,在一個ICO平臺上,最活躍的一個產品是專門諷刺ICO的。”
比特幣被認為是區塊鏈1.0,以太坊被認為區塊鏈2.0,這似乎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一件事兒。在眾人紛紛開始從比特幣轉向區塊鏈的時候,Jeffrey卻依舊屢次選擇為比特幣發聲,他表示因為至今為止,除了比特幣之外,沒有一個項目讓他覺得有足夠的顛覆性。
“去年ICO瘋狂的時候,每場峰會/會議都在討論區塊鏈,我是唯一一個還在聊比特幣的,然而現在比特幣市值占比又重新回到了50%以上,事實證明比特幣這個沒有融過一分錢的項目,還是笑到了最后。”
“我沒有反對區塊鏈技術,但是我是不贊成ICO的。ICO這樣的模式沒辦法避免團隊的不作為,團隊應該通過實現他們在白皮書中的承諾而獲得融資,而不是僅僅就寫了一篇白皮書,就成為了百萬富翁。在做出成績之前,尤其是在沒有公開協議的情況下,沒人應該獲得一分錢!哪怕是一分錢!”
ICO長期價值并不高,短期來說它是會產生一些價值。每當一個項目誕生,投機者們就報以一夜漲10倍的期望,這就意味著你的生態需要以10倍的速度在增長,而這種長期往往是存活不下來的。真正能夠存活下來的,都是以價值投資為導向的,需要有合理的治理機制。但大多數投機者完全不在乎治理機制,他們甚至連項目是什么都不在乎,他們只在乎誰站了臺,背景好不好,能不能拿到內部價,然后坐等上交易所拋售,他們根本不在乎項目后續發展。”
針對ICO這種融資模式是否會持久以及未來如何發展的問題,Jeffrey表示期望交易所能夠起到信息揭露義務以及公示上幣下幣規則,如果我們參考一下傳統模式,一個項目從萌芽到消亡的整個過程,會涉及到融資流程,破產流程,到最后每個人都是得到了自己該得的,盡了自己該盡的,這是一條標準線,而在數字貨幣這里領域也應該有這么一套規則,從而確保保障了每個人的利益。去年很多資金涌入,并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有多了解,而是因為他們覺得正是在風口上,現在冷下來之后,投資人會變得更聰明,更謹慎。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從區塊鏈看應用還是從應用想區塊鏈?
由于區塊鏈的爆紅,很多人在涌入區塊鏈領域之時,先披上了區塊鏈的新衣,再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資源可以契合,于是一個新瓶裝舊酒的區塊鏈項目便堂而皇之地誕生了。
Jeffrey認為真正應該關心的并不是技術本身或者是工具本身有什么特性,而是最終的目標是什么,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實現目標,而現在區塊鏈就是一個工具而不是目的。痛點是什么?問題是什么?要用什么相對應的工具去解決它,而不是先看好某個工具再去看領域里有什么一些好機會。
“如果你想建一個中心化的應用,你沒有理由要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我見過太多的項目完全無需用到區塊鏈技術,之所以要扯上區塊鏈這個概念,只不過是為了找個理由做ICO。如果我能用傳統方式復制一個項目,那這個項目就是偽區塊鏈項目。這是我沒法妥協的,在中心化的世界,我們都成了奴隸。美國三大巨頭Facebook,Google,Apple都會手機你的銀行卡信息等資料,最終總有那么一兩家公司會了解我們基本上全部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最終又會控制你,政府對這一切知情嗎?當然知道,最后的最后,這些所謂的巨頭又成為了政府的左膀右臂。”
“我始終強調的是信息主權,我們不應該這么輕易地免費地就舍棄了。有一個問題是Facebook到底有什么價值?Facebook擁有大量的用戶數據,能夠把用戶數據來作為變現。但是作為個人的用戶,為Facebook貢獻了個人的用戶數據,Facebook成為了整個生態的完全獲益者,而個人用戶跟Facebook在談判的時候沒有任何的談判籌碼。
為什么我們平時在一個公司工作能夠獲得報酬,但是付出我們的數據卻不能得到報酬?這里面一個本質的因素就是談判籌碼的設計,大公司站我了所有數據的主權,即使我們并沒有真正授權給他們進行售賣。區塊鏈技術是非常有意思的工具,它能夠潛在的將我們從這種關系當中解脫出來,使得我們能夠擁有自己的數據,然后在這個新的情況中跟大平臺相比有比較好的談判籌碼。”
尋找“黑天鵝”—我為何會投資Uber,Airbnb?
除了比特幣早期投資人的身份之外,Jeffrey還參與了現象級產品Uber,Airbnb的早期投資,對于這兩個項目的投資,Jeffrey表示其實并非他去找項目,也不是項目來找他。
“作為一個紐約人,尤其是碰上下雨天什么的,你會發現在你不需要出租車的時候,它隨處可見,但當你需要它的時候,它又一輛沒有。被迫無奈,你只能求助于高昂的汽車服務,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汽車服務也需要等上1-2小時,因為服務公司的車總是有限的。所以我就在想有沒有辦法讓更多不僅限于出租車公司的車,在市場上流通起來。而這個道理套在房地產上也是同的,所以在Uber和Airbnb誕生的一年前,我告訴我所有的律師Uber這種共享模式。我不在乎錢,我在乎的是學習。我一直說我自己很懶,我懶得去做項目,但我樂于將我的想法分享出去。這就是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有一個想法,交給別人去做,成了,我便繼續尋找下一個項目。幸運的是,一年后,Uber和Airbnb就誕生了,我的律師們爭取到了相應份額,并預留了部分給我。”
在Uber,Airbnb等產品大火之后,共享經濟也同樣大熱起來,然而Jeffrey則表示“Uber等不是共享經濟,而是匹配經濟(matching economy)。”
“Uber和Airbnb不是共享經濟,因為其價值沒有被共享,如果要說也應該是是匹配經濟,它是將不相關的兩個需求方牽連起來。那如何真正共享,代幣化就是很好的一個補充,它將每個利益相關者轉換為債權持有者。他們可能沒有擁有等值的債權,但每個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如果我們建立的是一個乘客可以獲得代幣、司機可以獲得代幣、參與該生態系統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向生態系統貢獻價值來獲得代幣、大家一起共享的生態系統,這才是共享經濟。”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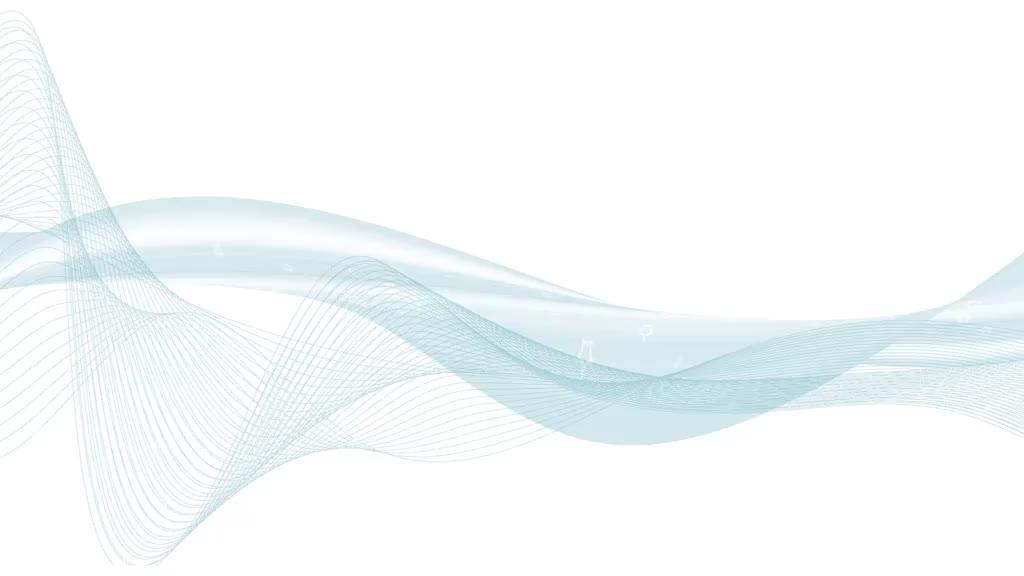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