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字化轉型成為國策,數字政府被打造為“一號工程”,各類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像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雖然最早這個概念由IBM提出并延伸,但似乎西方不亮東方亮,中國的各類應用和方案跑的更快。
大企業帶資入場,依靠集團財務實力和政府資源,能迅速拿下地方政府項目,但小廠商依托垂直技術只能單點突破,甚至最后不得不站隊抱上大腿,因為城市級解決方案的天性決定了單點突破不是最終的需求。
也因此,“平臺化”成為了智慧城市各大玩家的首選,也成為當前智慧城市領域最明顯的趨勢,當然,滴滴、UBER的成功也都是這種玩法。這其間,中小廠商在短期內是各大平臺型廠商爭奪資源的對象,但后期資源飽和,勢必也會面臨轉型的思考。
平臺的競賽
城市是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但更多的是服務的綜合,比如醫療、教育、金融、交通、民生、環保、能源、安防、地產等,這些單獨的領域實際上大都出現過巨頭公司,他們提供的方案讓城市管理者們欣喜:終于,城市病得到了緩解,智慧交通讓路況好轉,能源監測讓流失減少,金融科技提高安全系數。..。..
但是,在經歷過城市信息化進程并正式步入新興智慧城市階段,各種單點應用之間的關聯系數在快速提升,彼此不能孤立存在。
因此,城市管理者從治理、營商、民生三個角度綜合來看,需要能“一下子搞定”的方案,一步到位,一勞永逸。這就是目前智慧城市千帆競渡的獨特景象,誰沖到最前面,就能領先,而我們知道,大船的馬力足以支撐他們最先抵達。
研究機構和標準化組織在智慧城市領域起到的是“頂層設計”的作用,但真正的將技術沉淀到每一寸土地,主力還是各大互聯網科技公司,以阿里、騰訊、百度、平安、京東、華為、浪潮、商湯、云從等公司的“平臺化”趨勢最為明顯。
阿里打造的平臺是“ET城市大腦”,技術架構上分布著4個平臺:一體化計算平臺、數據資源平臺、智能平臺、應用支撐平臺。其背后,是強勢的云計算和AI技術做支撐。
騰訊推出的最新戰略是“WeCity未來城市解決方案”,相比之前版本的“城市超級大腦”做了升階,用微信、小程序等應用進行數字政務、城市治理等方案的落地。大部分技術來源自建,行業應用部分對方開放。
百度則倡導的是“AI City”智能城市的概念,利用最擅長的交通優勢切入,推動自動駕駛的落地。車路協同+自動駕駛是百度的打法基礎。
華為提出的平臺方案是“數字平臺”,對云、大數據、GIS、視頻云等實現統籌。畢竟,華為智慧城市的優勢在底層基礎設施,安防也是一大亮點業務,多年ICT的積累正在釋放這種優勢。
平安從金融這種壁壘性的優勢切入,提出“1+N”平臺體系,不做硬件,只做技術支持,一朵智慧城市云+N個行業板塊,把數據治理列為重點。
京東在打造“城市操作系統”上狠下決心,推出“城市計算平臺”,對城市數據的流動性設置了4個梯次,將時空數據作為面向未來的良藥。
而AI獨角獸領域的商湯科技和云從科技,都是從“視覺中樞”這個領域切入。商湯在近期推出的智能城市能力開放平臺方舟2.0,也在構建平臺之路上漸行漸深。
細分資源爭奪
平臺是最基礎的事情,巨頭們依靠自有業務積累,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搭建好,但是打通上下游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就需要提到小米公司。
有人說,小米的成功在于他的生態鏈形成了壁壘,加上小米的市值與財力超過了生態鏈企業幾十甚至數百倍,平臺不可能被顛覆,所以小米能在IoT領域做大。而類比到智慧城市,大家都在強調一種“生態”的玩法,其實根本目的就是把中小廠商的資源全部“圈進來”。
大廠在中標政府項目后,一般是總包再分包下去,因為平臺的能力獲得了信任。而在這之后的過程中,大廠實際上承擔起了管理和運營的角色,中小垂直公司就是具體的建設力量了。以交通為例,有諸多停車、車牌識別、車燈管理、路標識別、車流管控、乘車碼、人臉識別、定位導航等場景,BAT無暇分身,細粒度高的工作都是應用層的合作伙伴們完成。
因為,當平臺最上層的合作生態圈地成功,平臺的綜合實力就基本完善,復制、推廣的難度系數就會下降。
復雜的阻力
“方案復制”、“平臺遷移”,是大廠最終走向規模化必須跨越的關口。
因為,城市落地是政策+經濟+地理環境+技術的綜合表現,而技術的重要程度在這里排到了最后。也因此,我們看到,阿里在杭州、百度在北京、華為&平安在深圳、騰訊在廣東、京東在福建、浪潮在濟南等的落地,都是這些因素的最終體現。
當各大廠商深入到對方的腹地,施展“一城一策”的威力時,會發現政策障礙是最大的受挫原因。那些在雄安、粵港澳大灣區率先起跑的公司,或多或少在政府資源上是過硬的。
此外,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保證相關的技術更快落地。香港、澳門政府相對弱勢,或者受制衡的因素比較多,步子會稍慢一點。
此前雷鋒網在專訪 IEEE Fellow、澳門大學科技學院院長 & 計算與信息科學講座教授須成忠時,他就談到實現智慧城市的發展,一個必不可少的關注點是數據智能。他覺得,在做完頂層設計之后,具體實施階段的阻力并不是來自于平臺,并不是來自于數據中心和網絡,而是來自于數據的開放共享(解決數據孤島難題)。
當然,人才是又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子。阿里達摩院一批交通、視覺領域大牛聚齊,基本以IEEE Fellow為標準;京東城市計算也全方位招募人才,業界首次成立智能城市研究院,清一色兩院院士;百度、滴滴等都有相應的AI實驗室;騰訊以產業互聯網為核心,從工業、零售、醫療等具體場景擴充團隊,把懂互聯網和懂行業作為必備技能。
調整航向
除了大廠本身的研究力量,高端學術研究領域的新動態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也是大廠最終實現“平臺增長”的食糧。
在地理信息這一派,中國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認為,GIS是智慧城市的操作系統,因為智慧城市階段,時空基準將被建立,時空大數據將爆發,時空信息云平臺將是更大平臺的必備能力項。
在城市計算這一派,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院長鄭宇博士則提出基于AI和大數據能力的城市操作系統,向不同的云計算平臺開放,利用6個時空數據模型收納城市萬千數據。
在AI學術這一派,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教授潘云鶴認為,大數據智能現在只是一個開始,后面還有很多新技術和模型要發展出來。大數據智能、群體智能、跨媒體智能、人機混合增強智能、自主智能系統這五個方面將在今后幾年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中有巨大的突破。
我們因此也看到,在通往智慧城市之路上,身邊一直流動著新的思考。
抵達“理想國”
綜合來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與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經濟發展等相依相存,彼此成為抓手,互為轉型動力。
大面積、大資本、大項目,勢必決定著大平臺的呼之欲出。
但在大平臺的光鮮亮麗之下,優秀的垂直解決方案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當前解決城市問題的“釘子”與“錘子”,沒有他們,城市管理者就不會為沒有實質方案的“框架”買單。
2019年是建國70周年,是我國各項事業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關鍵節點,改革步入深水區,城市更加數據化。而智慧城市是下一個10年的重點,是典型的政產學研必須勠力同心來進行的大項目,勢必需要前瞻性的觀點支撐著后續的方向。
因此,2019年7月13日-14日,由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雷鋒網、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聯合承辦的第四屆CCF-GAIR全球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峰會,將開設「智慧城市」專場,探討未來城市頂層設計、城市云計算、數據治理、城市AI視覺智能等解決方案的核心技術與場景實踐。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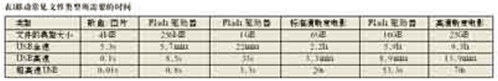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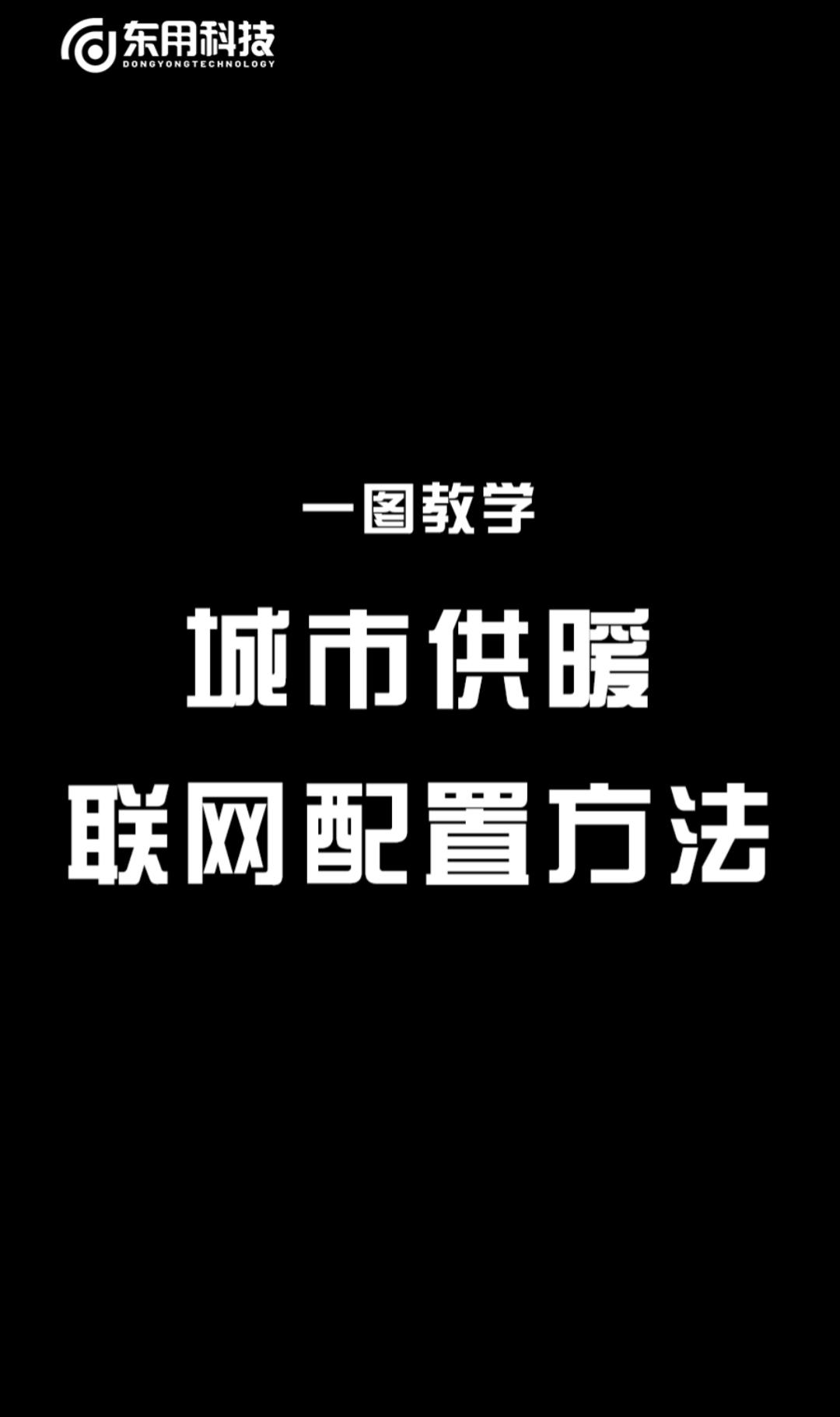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