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是一個泛稱,廣義上指對真實自然及未知生命、環境、現象及其相關現象統一性的數字化重現與認識、探索、實踐、定義的專業類別貢獻者。
狹義的定義是指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士,包括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這兩大類。如被稱之為科學家的代表人物有英國物理學家牛頓、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居里夫人,美籍科學家愛因斯坦和中國的農學家袁隆平等。
因此在現在的科學環境下,對于一個有志于成為科學家,準備獻身科學研究的年輕人來講就必須注意一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認識到科學的重要性,認同科學是人類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有了這樣的觀念才會熱愛科學,才會產生獻身科學的動機和愿望。
二,自覺培養科學精神,盡可能地系統掌握已有的科學知識。其實這是一個科學家所必不可缺的東西。
三,鑒于現在大科學的特點,如何最在經過一番努力之后成為科學家還需要一定的策略。
回想過去,多少曾經的科學幻想如今已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今天的我們,對未來也有著種種的科學期盼和人文關懷。小到人體細胞,大至整個宇宙,玄到意識到起源,編者盤點了20種科技疑問,下面請看20位科學家的經典回答。
1. 當地球的壽命結束,人類能夠繼續生存么?
我認為大規模從地球移民出去的設想是一個很危險的錯覺。在太陽系中,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比甚至珠峰峰頂或者南極點更為適宜人類。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存在這一問題。不過,我推測到下個世紀,將出現由私有團體資助的火星探險生活,之后可能還會拓展在太陽系的其他地方。
我們當然應該預祝這些先驅開拓者交上好運,要知道他們是依靠著各種機械技術和生物科技來適應外星環境。在幾百年后,他們將演變為新的物種:后人類時代即將開啟。超越太陽系的旅行則是后人類的事業,無論那是否需要他們親力而為。
—Martin Rees, British cosmologist and astrophysicist
2. 我們什么時候,在哪里能夠找到地外生命?
如果在火星上存在著大量微生物的話,我估計在20年內將找到類似我們人類形式的生命。如果地外生命和地球上的物種存在較大差異,那么尋找難度將會較大。當然也有可能火星上幸存的微生物比較稀少并且存活位置難以讓我們的機械探測器抵達。
木星的衛星歐羅巴和土星的衛星泰坦 (土衛六) 也是值得關注的地方。歐羅巴作為一個水的世界,可能會進化出更復雜的生命形式。泰坦大概是太陽系中可能存在生命的最有趣的地方。那里富含有機分子,環境很冷且沒有液態水。如果存在生命,那么一定和地球上的物種大為不同。
—Carol E. Cleland, philosophy professor and co-investigator in the Center for Astro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3. 我們能否理解意識的本質?
很多哲學家、神秘主義者等等都認為我們無法最終理解意識或者主觀思想的本質。不過沒有理論可以支持這樣的失敗主義論調,我們也有很多理由去期待那一天,在不遠的將來,科學將成為一種馴化的,量化的,對于意識和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預測性的認知能力。
—Christof Koch, president and CSO at the 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 member of the Scientific American Board of Advisers
4. 是否會有那么一天,這個世界擁有足夠的醫療服務嗎?
在過去25年中,全球共同體已在醫療公平性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過這些成績還沒有覆蓋到世界上那些最偏遠的群體。深入熱帶雨林,那里的人們與世隔絕,沒有交通,沒有網絡,可用的醫療服務最少,護理水平最低,死亡率居全球最高。據世衛組織估計,大概有10億人因為路途遙遠,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醫療人員。
直接從當地社群招募衛生保健人員可以填補這一缺口。他們甚至可以抗擊埃博拉這樣的傳染病,在醫療機構不得不關門的時候保證基本護理的到位。我所在的機構Last Mile Health利比亞政府合作,在九個行政區的300個社區部署了300多名保健人員。但是我們無法單獨完成這一工作。如果全球共同體對全人類醫療保障是重視的,那么必須投資從而保證醫療人員能夠抵達那些偏遠地區。
—Raj Panjabi, co-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at Last Mile Health and instruct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5.腦科學能否改變刑法?
基本來講,大腦就是一臺體現因果律的機器。其功能即根據先行條件,從一個狀態轉變為另一個狀態。刑法與此的關聯完全是不存在的。首先,所有的哺乳動物和鳥類都有自我控制的回路,這可以通過強化學習來改變 (做出好的選擇會得到獎賞),特別是在社會環境下。
刑法涉及的是公共安全與福利。即使我們能夠識別那些特殊的回路,比如連環兒童強奸犯,限制他們的自由,因為他們傾向于再犯。是否我們就可以說,“他有那樣一個大腦不是他的錯,放他回家吧。”這無疑是一種私自執法行為。當這樣粗暴的審判替代了已經扎根多年力求公平的刑法系統,事情會變得很糟糕。
—Patricia Churchlan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6.人類在未來500年生存下去的希望有多大?
我想我們生存下去的幾率還是很不錯的。即便重大危機——比如核戰爭或者氣候變化之后的生態災難——也不至于將我們完全清除。目前的一個威脅是,機器將超越人類并決定脫離我們而存在下去。面對這個問題,至少我們可以拔掉它們的電源。
—Carlton Cave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physics and astr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7. 我們能否防止一場核浩劫?
在911事件后,美國的一大主要策略就是通過加強富鈾富钚地區的安全,并盡量鏟除恐怖分子來減少核恐怖主義的威脅。一次核恐怖主義襲擊可以奪去10萬人的生命。冷戰結束后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然而在美俄的核對抗中仍埋藏著巨大的核浩劫危險。這涉及到上千次的核爆炸,以及無數生命的當即隕滅。
就像珍珠港事件,美國如今已經表明在假想情況下,其所有核力量有可能被俄羅斯先發制人的閃電戰一掃而光。我們當然不想遭遇這樣一次攻擊,但雙方都保持著洲際和潛艇導彈發射能力,各有1000枚左右的彈頭處于預警發射狀態。由于導彈的飛行時間只有15到30分鐘,所有關系到億萬人生命的決策必須在幾分鐘之內做出。這就帶來了偶發核戰爭甚至黑客引起導彈發射的很大可能性。
美國并不需要做出這種威懾姿態,因為在它那些無法被鎖定目標的潛艇上載有800枚彈頭。如果發生核戰爭,美國和俄羅斯都希望在他們脆弱的陸地導彈系統被摧毀前發揮其功用。冷戰雖然過去了,但這種末日機器依然伴隨著我們,一觸即發。
—Frank von Hippel, emeritus professor at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co-founder of Princeton’s Program on 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8. 人類的性活動是否會衰退?
不太會。但通過性行為孕育后代的方式可能會變得不再那么常見。在未來20-40年中,我們將能夠從干細胞中獲得卵子和精子,這很可能來自雙親的皮膚細胞。這將允許我們在胚胎植入前對其進行基因診斷,或者為那些希望對胚胎進行基因編輯的父母提供服務。
—Henry Greel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9. 會否有一天,我們能夠依靠工程學替換所有人體組織?
在1995年,我和Joseph Vacanti曾撰文介紹過人工胰腺技術,以及塑料材質的人工器官和電子器件的發展,甚至能夠使盲人復明。如今這些都已不為人所陌生,不是變成了真實產品,就是進入了臨床試驗。在未來幾個世紀中,很可能任意的人體組織都能夠通過這樣的途徑被替代。培養或創造大腦這樣復雜而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組織將需要大量的研究。然而相關研究將很快幫助治療腦部疾病,比如帕金森或者阿爾茨海默癥。
—Robert Langer, David H. Koch Institute Professor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0. 我們能否躲過“第六次大滅絕”?
如果我們快速采取行動,這可以被延緩,進而停止。物種滅絕的最大原因是棲息地的喪失。這就是為什么我要強調一個完整的全球保護區,包括一半陸地,一半海洋。在這一倡議下,我們還需要去發現并鑒定那近千萬個尚存且未知的物種。目前,我們只發現并命名了200萬種。總之,包括生物界在內的環境科學的延伸,應當是本世紀剩余時間中的一個主要科學目標。
—Edward O. Wilson, University Research Professor emeritus at Harvard University
11. 我們能否養活所有人而不必毀掉地球?
可以的。人們應該這樣做:減少作物廢料、生活垃圾以及肉類消耗;結合恰當的種子技術和管理實踐;幫助消費者了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農民所面臨的挑戰;提高農業研究和發展的公共資金;從社會經濟和環境角度重點推進可持續農業。
—Pamela Ronald, professor in the Genome Center and the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2. 我們能否在外太空開拓殖民地?
這要看“殖民”的定義。如果派機器人登陸就算的話,那我們已經做到了。如果是把地球上的微生物運過去,使它們生存甚至發展下去,那么很遺憾,我們還沒有做到。可能鳳凰號火星探測器和好奇號探測車最為接近,它們都配有熱源,但離維京人那種殖民還差得遠。
如果這意味著人類在其他地方生存一段較長的時間,但不繁衍后代,那么在未來50年內很可能會實現。(雖然有所限制的繁殖活動是可行的) 但是目標是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環境,使人類可以在地球的少許幫助下即可無期限地生存下去,那么這種定義下的“殖民”還很遙遠。我們現在還遠遠無法掌握該如何構建封閉式生態系統,能夠很好地抵御外來有機體或非生物學事件 (如“生物圈二號”)。我認為這種生態系統問題所面臨的挑戰比太空殖民擁護者以為的要難得多。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題有很多,另一個問題就是空氣處理。我們還沒有在地球上嘗試過水下殖民。要征服一個甚至沒有大氣層的環境恐怕要困得的多。
—Catharine A. Conley, NASA planetary protection officer
13. 我們能找到一個地球的孿生兄弟?
我打賭可以。相比于幾十年前,我們發現的圍繞其他恒星運行的行星已經多了很多。而且我們已經發現在地球上對于生命至關重要的成分——水——在太空里也比較常見。我想大自然對于很多行星都有所青睞,包括類地行星。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去尋找它們。
—Aki Roberge, research astrophysicist focusing on exoplanets at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14. 我們能治療阿爾茨海默癥嗎?
我不確定是否真會有一個治療方法,不過我非常希望在未來十年中針對阿爾茨海默癥能夠出現一個成功的疾病修飾療法。我們已經開始進行預防實驗,甚至在人們出行臨床癥狀前就進行生物干預。其實我們不必完全治愈阿爾茨海默癥,我們只需要將老年癡呆表現延緩5到10年就很好。據估計,如果嚴重的病癥階段延緩5年,將減少近50%的醫療保障負擔。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將能夠在外部環境安心地離去,而不是在病房中。
—Reisa Sperling, professor of neurolog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lzheim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5. 能否出現可穿戴技術設備來探測我們的情緒?
情緒涉及到抵達我們身體各器官的生化和電信號,比如壓力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可穿戴技術使我們可以在較長時段內對這些信號的模式進行量化。
在未來十年中,可穿戴設備將能夠為我們的健康提供個性化天氣預報:根據你近期的壓力、睡眠、社交情感活動等判斷,你的健康和快樂概率將提高80%。然而,與天氣預報不同,智能穿戴設備還能識別出我們緩解“風暴”事件的方法:保持每天9小時以上睡眠,保持當前的中低水平壓力,那么在未來4天內發飆的幾率可降低60%。在接下來20年里,可穿戴設備以及其帶來的分析結果,將大幅減少我們的精神和神經疾病。
—Rosalind Picard,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Affective Computing research group at the M.I.T. Media Lab
16. 我們能否弄清到底什么是暗物質?
我們是否能確定暗物質是什么取決于它到底是什么。有些形式的暗物質允許在探測與普通物質之間發生微小的相互作用,這在以往都避開了探測。其他暗物質則可能通過其對星系等結構的影響從而被探測到。希望我們能夠從實驗或觀測中學到更多東西,但這也不是一定能保證的。
—Lisa Randall, Frank B. Baird, Jr., professor of science in theoretical physics and cosm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17. 我們是否能夠掌控諸如精神分裂或者自卑癥這樣棘手的腦疾病?
像精神分裂癥和自閉癥這樣的疾病一直是我們沒有解決的,因為神經科學還沒有找到其結構性問題進行修復。有些人認為未來的答案將完全在生物化學中找到,而非神經回路。有些人則認為神經科學家應該從整體大腦構造入手,而不是特定的神經障礙。當我暢想未來的時候,總會想起諾貝爾獎獲得者Charles Townes的名言:一個新理念的精彩之處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會是什么。
—Michael Gazzaniga, director of the SAG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Min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8. 隨著技術的發展,藥物研發能否不再需要動物實驗?
如果器官芯片能夠在世界各個獨立實驗室中展現出良好的技能,替代復雜的人體器官生理學,解決病理表現,那么正如以前概念驗證研究指出的那樣,這將能夠逐步替代動物模式,最終大幅減少動物實驗的需要。重要的是,這些設備將為藥物研發開啟新途徑,而這在今天的動物模式中是無法實現的。比如個性化醫藥,以及來自特殊雙親細胞制造的芯片中特定基因亞群的醫療研發。
—Donald E. Ingber, founding director, Wyss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ly Inspired Engineering at Harvard University
19. 在科學領域能否實現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可以實現,但我們不能只是坐等它自行發生。我們需要招募更多的女性到科研和技術領域中來,從而“拉平數字”。我們應該讓機構執行“雙職工”策略,推進家庭友好仿真,幫助領導人開拓新視野。最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利用關于不同性別發現和創新能力的分析來完善這方面的認知。
—Londa Schiebinger, John L. Hinds Professor of History of Scie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20. 人類是否有一天能夠提前幾天或幾小時預測像地震這樣的自然災害?
有些自然災害較其他更容易預測。颶風需要幾天才會到來,火山需要積聚幾天或者幾小時才會噴發,龍卷風則僅需要幾分鐘就能席卷而來。地震可能是最大的挑戰了。通過對地震本質的了解我們知道,提前幾天預測地震大概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可以在地震來襲前幾秒甚至幾分鐘預測將遭受破壞的地區。這不足以讓我們離開城市,但能夠讓我們尋找一個安全之所。
—Richard M. Allen, director, Berkeley Seismological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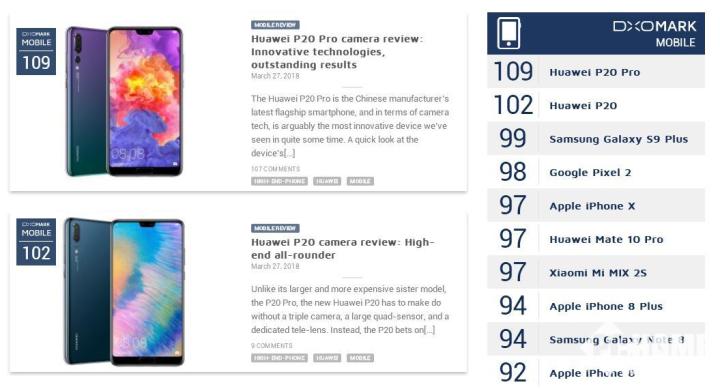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