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軍備競賽”箭在弦上,只不過這一次,主角從熱兵器變成了高科技產業。
5G商用牌照較預期提前發放,給運營商的建設布局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國三大運營商一齊轉向了NSA,在全球范圍的5G競爭上由”SA爭先策略”變成了“NSA跟隨”。萬物互聯何時才能成為現實?
“5G競賽是一場美國必須要贏的比賽。我們是有敵人的,要確保5G不被敵人掌握。”美東時間4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宮吹響了以5G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競賽的號角。
北京方面的回應有力又不失風度,當地時間6月5日,《人民日報》在其官方推特上宣布,中國將于6月6日發放5G商用牌照。
回顧過往,我們會發現近年來美國對中國通信企業的打壓和圍堵頻頻發生。
從去年4月中興再遭封殺、華為被禁入場,到去年年底華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羈押、所謂的“五眼聯盟”先后對華為的5G設備和技術發出“禁令”,再到今年3月以所謂的“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向德國、加拿大等盟友施壓,要求這些國家將華為排除在本國5G網絡建設之外。
究其原因,這是“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帶來的必然性事件,幾乎避無可避。用特朗普政府的話說就是,新一輪的“軍備競賽”箭在弦上,只不過這一次,主角從熱兵器變成了高科技產業。
5G背后的暗涌流動
此前業界的預期是,5G試商用牌照將于9月發放,而正式的商用牌照至少要等到2020年。
此次工信部取消臨時牌照環節,跳過5G試商用階段,直接發放正式牌照,標志著我國正式進入5G時代,比原計劃提前了一年。
時間走到2019年,全球進入5G商用部署的關鍵期。無論是上海、廣州、重慶、濟南等地陸續開展的5G自動駕駛巴士、5G機場、5G寬帶等測試項目,還是MWC 2019上密集釋放的5G亮點,抑或是前幾天BBC使用5G網絡直播的早間節目,無不預示著世界通訊發展史正在翻開新的篇章。
可我們所說的“正在”,并不屬于一個完成時態。遺憾的是,隨著中美貿易沖突日趨激化,關于5G主導權的爭奪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含義——大國博弈的工具。
而這一切,其實早有端倪。
從1G到4G,從摩托羅拉制霸全球到諾基亞、愛立信的興起,美國和歐洲一直是唱對臺戲的。在5G時代,他們終于走到了一起——以打擊華為作為橋梁。美國政府一句“國家安全”就讓華為失去了大部分歐洲市場,歐洲的5G項目幾乎盡入愛立信之手。
要知道,歐洲可是華為的傳統市場。
于是我們看到華為的運營商業務一落千丈,去年的收入同比減少1.3%,而這個數字前幾年還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長。根據IHS Markit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華為在移動通信基礎設施的全球份額上被愛立信反超。
然而損人,就能利己了嗎?
根據GSMA的行業分析報告,“全面禁止中國通信設備供應商華為和中興通訊對歐洲推出5G網絡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將達到550億歐元(約620億美元,4287億人民幣),并將導致該技術的推出延遲18個月左右”,報告還指出,“此種延遲將使歐盟與美國之間的5G普及率差距在2025年前擴大15個百分點。”
今年5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促使包括高通、ARM、谷歌、微軟在內的多家科技巨頭切斷了與華為的聯系。然而他們需要付出的代價,除了數額龐大的機會成本,還有難以估量的商譽減持風險。
今天是華為,明天就有可能是任何人,畢竟誰都不想一覺醒來就沒法用自己早已付過錢的安卓和Windows。
5G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人們所描繪的那個“信息隨心至,萬物觸手及”的互聯世界,不過美利堅利用政治力量封鎖中國公司的行為,似乎一點也不“萬物互聯”。
電信運營商的“冰與火之歌”
5G牌照的發放對象,是移動、聯通和電信這三大傳統的電信運營商和新入局的廣電。
4月初,韓國和美國運營商搶跑全球5G商用,國人不免陷入“中國在5G競爭上是不是掉隊了”的焦慮之中。
對于身處5G產業鏈前端主導位置的通信運營商來說,壓力不可謂不大。
最初,選擇SA(獨立組網)標準部署5G網絡曾是中國通信業界,特別是通信運營商的普遍共識。在5G SA標準的制定過程中,中國移動不僅主導了5G第一個版本網絡總體架構標準的制定,還連續在去年2月份和6月份聯合華為、愛立信、諾基亞和英特爾等全球合作伙伴發起了“5G SA突破行動”和“5G SA啟航行動”,來推動SA標準的實現。
然而今年2月份,在巴塞羅那舉辦的GTI 2019國際產業峰會上,中國移動副總裁李正茂卻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國移動要在2019年啟動NSA(非獨立組網)的“規模部署”。
這大概和完全支持mMTC和uRLLC場景的R16標準按計劃要到2020年3月才能完成有關。最重要的一點是,NSA架構比SA架構更省錢,NSA組網下,5G基站將利用現有4G核心網,省去了5G核心網絡的建設費用。
多快好省,似乎沒有什么理由不選NSA。
這里要簡單解釋一下二者的區別,NSA的優勢在于產業進展略快,但它卻是不支持uRLLC(超高可靠低時延通信)和mMTC(大規模機器類通信)的場景。那這兩類場景包括什么呢?我們暢想的工業自動化、遠程醫療、無人駕駛、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環境監測盡在其中。
而中國電信也在3月份的財報發布會上宣布將5G策略由原來的“優先選擇獨立組網SA方案”調整為“同步推進NSA和SA發展”。再加上中國聯通受限于資金和技術實力早早選擇了初期投入較低的NSA,中國三大運營商一齊轉向了NSA,在全球范圍的5G競爭上由”SA爭先策略”變成了“NSA跟隨”。
聯想到海外5G產業鏈在NSA上形成的先發儲備,被動可想而知。頗有幾分虎頭蛇尾的意思,就像《權力的游戲》最終還是沒能沿著《冰與火之歌》的步子坐穩“王座”。
再從運營商的角度出發,從NSA過渡并最終演進到SA目標網絡,至少要對原有網絡進行3次復雜的改造,每一次都面臨著新一輪的成本投入和更復雜的網絡風險。
根據三大運營商歷年的資本開支情況,14、15年是他們近五年來的最大峰值,這也和4G網絡升級換代的時間節點相符。顯而易見的是,5G牌照發放后,三大運營商又將迎來一波投資高峰。
可在中國移動最新發布的2019年Q1報告中,由于受到收入同比下降和剛性支出持續增加的影響,2019年一季度公司的稅前利潤同比下降了8.6%。
在運營商固定資本支出的有限范圍內,每多投一塊錢到NSA,就意味著在SA建設上的投入少了一塊錢,我們離以SA驅動垂直行業變革的目標也就更遠了一步。
先2C后2B的邏輯,能自圓其說嗎
前面已經說過,NSA架構不支持uRLLC和mMTC的場景,那5G三大業務中碩果僅存的eMBB(增強移動帶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是對現有4G服務速率上的升級,也就是說,它面向的還是現有用戶體驗的提升。舉個例子,下載一部電影5秒鐘,這是聯通給出的官方說法。
不過,幾秒鐘Down一部電影,似乎也沒那么重要,更不必說這一切的代價是更高的流量消耗、更貴的通信資費,以及一部價格不菲的新手機。
在微博“工信部發放5G商用牌照,你會馬上換新手機嗎?”的投票下,最高票的回答是“先觀望一陣再說”。
而在其下的評論更是直接表明了網友的態度。
拋開社交媒體的態度,我們都知道的是,4G改變了生活,5G就是用來改變社會的。
而大家寄予厚望的創新領域,無論是自動駕駛,還是工業互聯網,抑或是智慧城市的建設,都是基于對物聯網海量連接的需求,但這恐怕不是僅靠高速率和低時延就能解決的問題。在信通院的報告中,大規模的物聯網應用暫無任何計劃,即使到2035年,真正的智能制造仍處于仍處于較早的發展階段。
更何況,這些想象空間欠缺的不只是海量連接這一步。以自動駕駛技術為例,它們受制于日常駕駛場景的復雜多樣,譬如現有的技術無法理解基本的道路基礎設施特征及駕駛任務,無法做出無保護措施下的左轉任務,也無法在匝道上的信號燈前停車。
NSA架構下的5G網絡,唯一合理的想象只存在于8k超高清視頻的傳輸,這大概是廣電能從三大運營商手中分一杯羹的秘訣所在。
自1990年施樂公司提出“Networked Coke Machine”的概念,已經過去快30年的時間了,迄今仍未出現殺手級的應用和大范圍爆發的應用場景。
技術突破本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知古鑒今,3G技術興起之初為移動行業繪制的用高速數據和視頻改變世界的理想畫面猶在眼前,然而現實卻是,3G設備未能激發消費者的興趣,3G技術最終也未能交付所謂的“殺手級應用”。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運營商減值、延期,3G成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均未成功的平臺。
目前看來,萬物互聯的市場剛需是存在的,只不過NSA架構下的5G不一定能消化。當然有一點還是可以消化的,那就是華為在歐洲市場沒能賣出去的NSA產品,畢竟對于一家企業來講,如此大規模的投資,還是盡快變現得好。
出口轉內銷,山人自有妙計。
其實,走得慢一些也不一定是什么壞事。我們4G商用的時間比美韓晚了兩年多,但我們不依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網絡,并成就了中國移動互聯網的黃金十年嗎?
大概不管是對工信部,還是三大運營商而言,5G都是“你有我也要有”的玩意兒吧。至于有沒有用這個問題,可以容后再議。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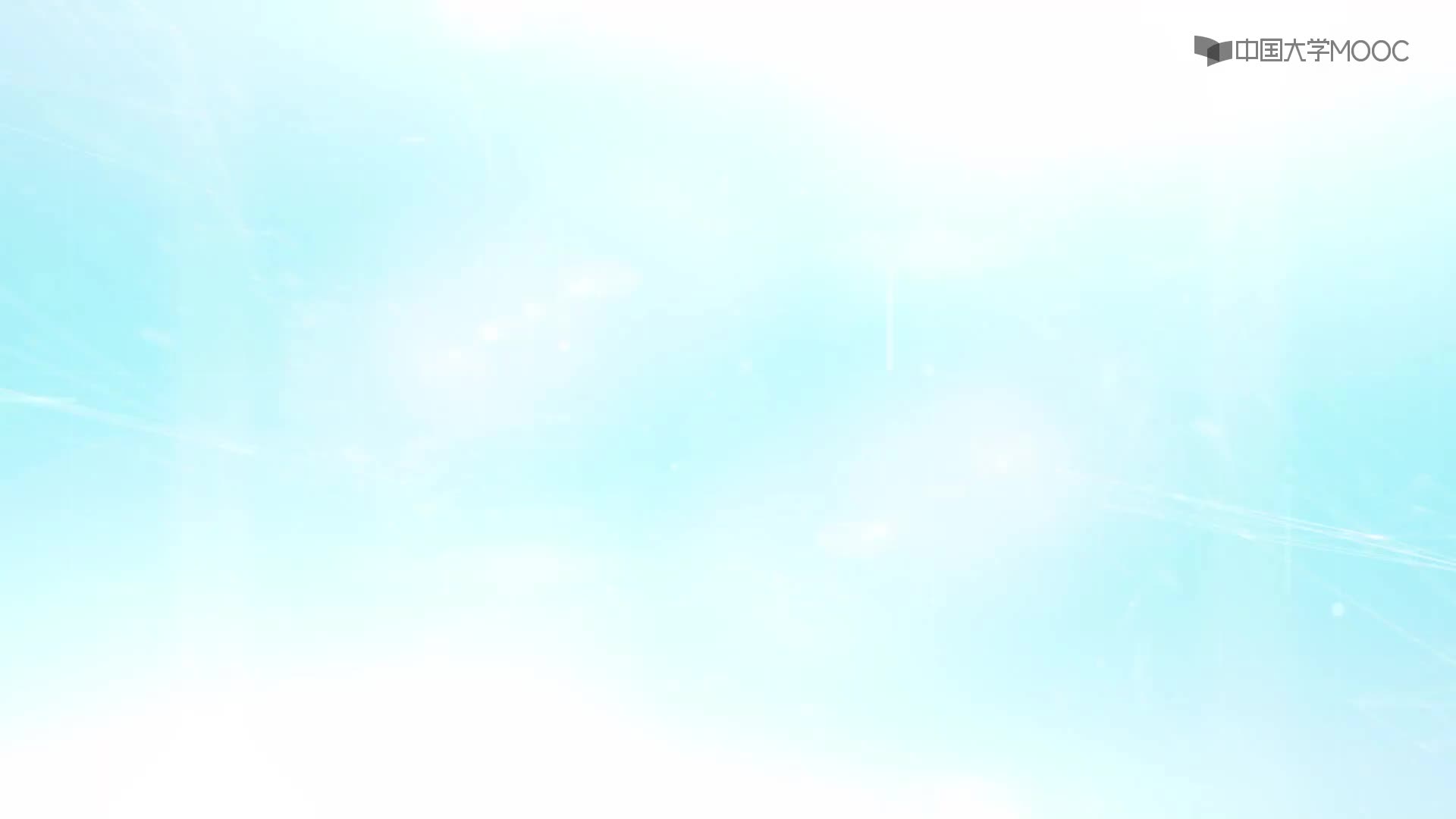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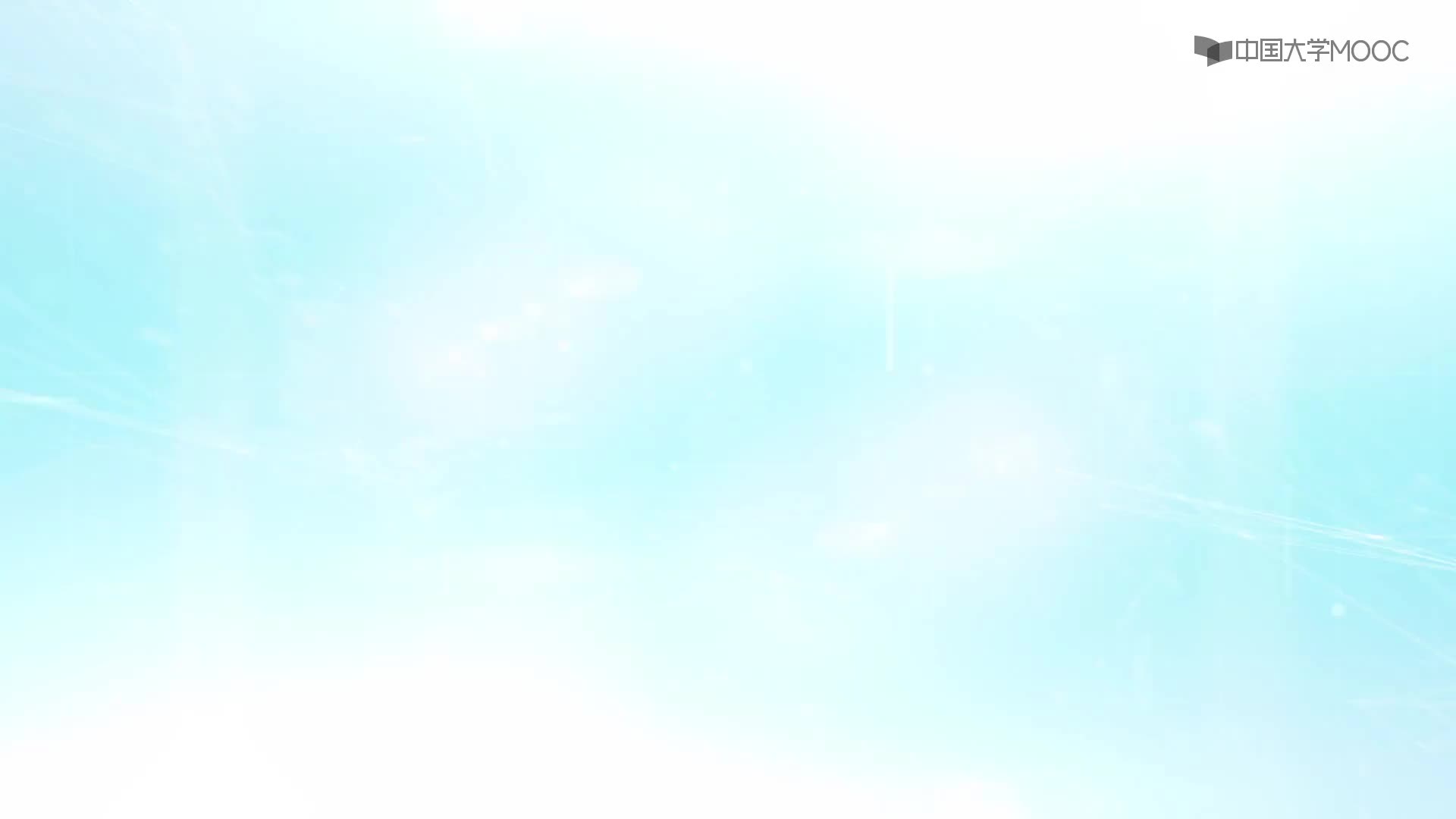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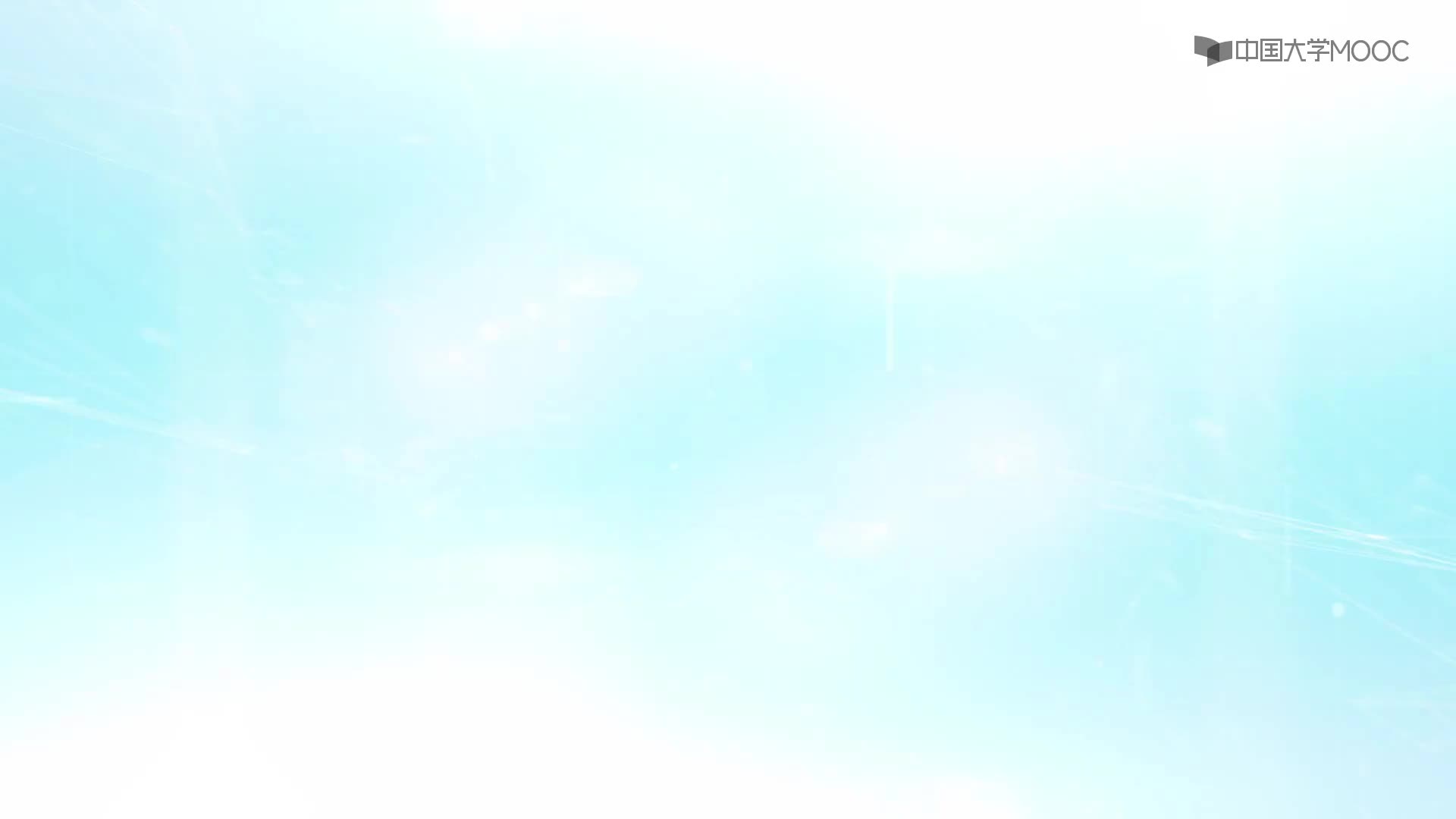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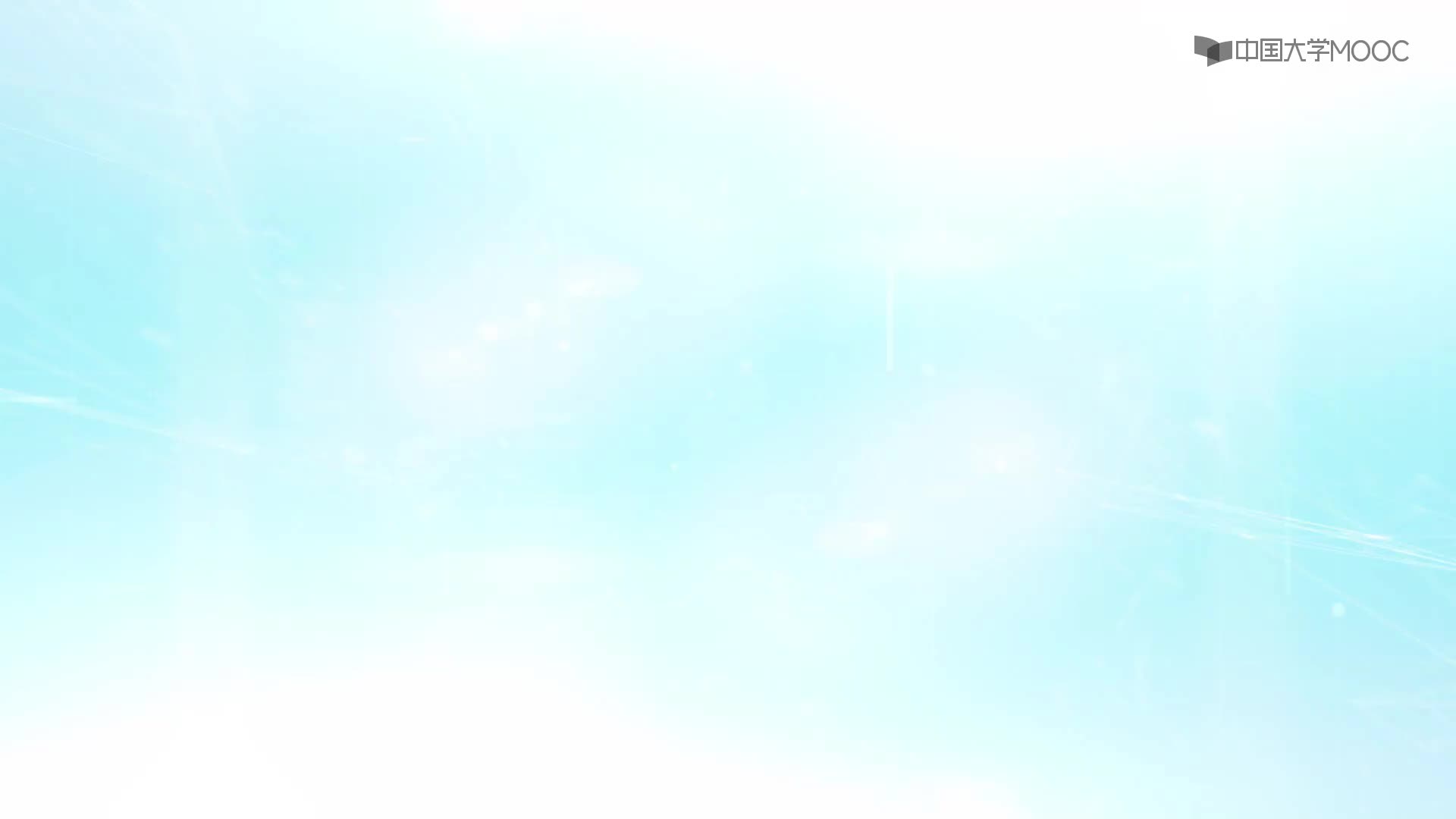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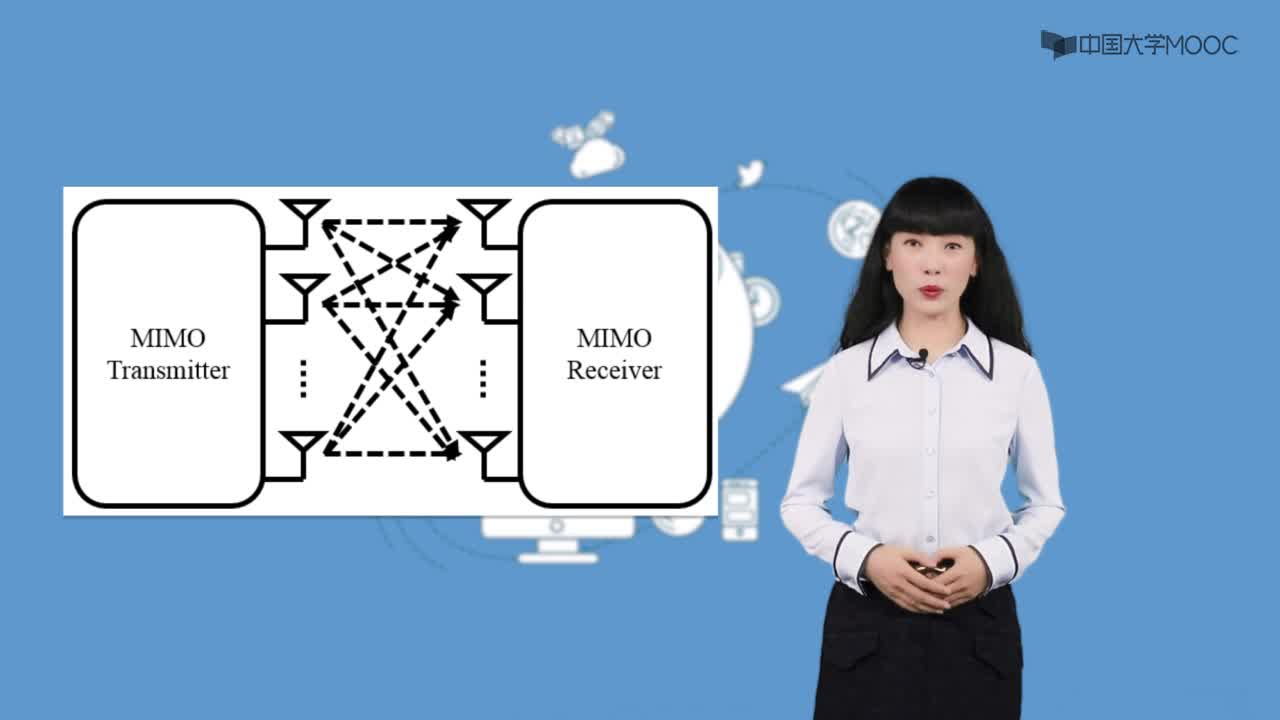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