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制造業自動化轉型升級的速度沒有趕上生產成本紅利消失的速度,不可避免出現了一個尷尬局面:工廠要跑了!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正面臨著來自生產成本比我們低很多的東南亞國家的挑戰。從國際形勢上開看,可能情況更嚴峻:美國的圍堵,東南亞、墨西哥的步步緊逼,真是“前有狼,后有虎”。
生死不入制造業
貿易戰是一記驚雷。
“所有人都很緊張,急速求變,從長計議,我們可能轉移所有東西。”美國旅行背包品牌TortugaBackpacks聯合創辦人佩羅塔說,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后,花了4年時間在中國建立了完整的生產商網絡的Tortuga Backpacks打算在越南尋找替代供應商。
一些專家斷定,這是繼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又一次最大的“跨境供應鏈轉移”。盡管主流媒體對制造業撤離諱莫如深,但是中國制造業加速向東南亞和印度遷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遷徙早在前幾年就已經出現。全球最大運動鞋制造商***寶成集團旗下裕元工業設于東莞高埗鎮的工廠,高峰期達10萬人左右,僅在2012年就砍掉51條制鞋生產線。與此同時,寶成在越南的廠區目前已經增加到7個,員工數約16萬人。
不僅是珠三角,在浙江溫州、福建晉江等制鞋基地都在轉移或關閉。“中國南部地區工資的上漲可能會迫使消費品的制造商將生產遷出,在未來五年迅速地轉往成本較低的地區,包括中國西部、印度尼西亞、越南和孟加拉國等。”利豐總裁BruceRockowitz早已預言了現在發生的事情。
3C電子行業也難逃此劫。最近,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已經計劃前往印度談判,將生產線轉移至那里。早在此前,郭臺銘就提出,到2020年,富士康在印度國內興建10至12家生產工廠,并創造至少100萬個就業機會。
與富士康、廣達電腦齊名的金仁寶集團也正在有計劃地撤離中國。2015年,集團旗下的孫公司泰金寶電子在春節前全面停產,在同一廠區的泰金寶光也結業,并已經將相關的設備材料轉出到泰國、巴西、波蘭等國。
同樣是在2015年,隨著三星在越南投資百億美元的生產基地相繼投產,三星電子將80%的中國產能轉移到越南的計劃正加快實施。
越南最大地產發展商之一的BWIndustrial公司表示,去年十月起收到許多查詢,目前所有工廠都已經被租走。
改革開放的40年進程中,強大的加工貿易曾為我們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今天我們的制造業至少面臨著訂單難、商品流通難、成本優勢不再、融資難的四大困境,甚至于很多老板在口口相傳著“生死不入制造業”的論調。
制造業撤離的危機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關于1791年制造業的報告》中闡述了一個永恒的原理:有志氣的,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往往感受到比較先進國家的重壓。“不僅國家的財富,而且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看來都與制造業的發達有著實質性關系。”
制造業的撤離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歷史在輪回。
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前,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是全球制造業老大。20世紀50年代,美國因為低附加值工作崗位的維持成本高于亞太地區,把自身淘汰的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日本。
20世紀60/70年代,日本又因為中國***、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的生產成本比自己低,又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
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亞洲四小龍”也開始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正在進行“改革開放”,兩邊一拍即合,大陸憑借當時低廉的生產成本和政府開出的優惠政策,吸引來了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成了“世界工廠”。
這之后又過了20多年,中國的生產成本不可避免地不斷上漲,而越南、印度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成本優勢逐漸顯露。
就像30年前我們很自然地承接了來自“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一樣,我們也要面對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現實。
制造業工廠撤離帶來的勞動就業問題其實已經顯現。
由于訂單外流,位于深圳優衣庫代工廠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工人已數月無班可加。該廠員工老李表示:“以前是每天正常上班8小時,再加班兩小時,基本是可以養家糊口的,但現在已經幾個月沒加過班,在扣除了社保等費用之后,我3個月的工資只有1354.77元。”
工資減少已經算是輕的,還有數以百萬計甚至更多的工人面臨著失業的問題。
建于1991年12月的奧林巴斯深圳工廠,有非常輝煌的歷史,在其鼎盛時期,有員工1.5萬人,但在宣布停工前,工廠只剩下1400名員工,而且很多年已經沒有新招工人。
勞動就業問題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也值得思索。工廠撤離,首當其沖的就是地方財政受到影響,而財政受到影響,隨著而來的便是社會福利降低、地方發展速度減緩等一系列問題。
大型制造業工廠撤離大陸,更將對與之相關的上下游產業產生重大沖擊。
猶記得2016年,三星打印機從威海遷移,整個高區哀鴻遍野。在三星遷移后,隨之遷移和倒閉的還有給三星配套的大量企業和第三產業。
去年4月,深圳三星電子通信公司宣布將被撤銷,與此同時,三星在中國的供應鏈也出現劇烈振蕩。首先是其一級供應商蘇州普光、東莞普光、東莞鎢珍、及艾迪斯等曾在中國雇傭成千上萬名員工的大廠先后倒閉。
緊接著,三星重要供應商友達光電員工們在工廠打出了“友達贏利十余年,一朝關廠見血淚,奸滑工廠討公道”的橫幅,以表達對工廠突襲式關廠的不滿。
可以想象,如果后續更多制造業工廠撤離中國,會造成多么巨大的損失。
事實上,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制造業萎縮的趨勢似乎發生了“逆轉”,許多人將此稱作美國制造業的回歸。
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他們的政策導向都旨在透過技術創新,推動高科技發展,引導高端制造業重回本土,鼓勵企業回到美國在本土建立工廠拉動就業。
一旦撤離,中國的制造業回歸,要多久?
中國制造業的成本紅利正在消失
成就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是什么?中國制造的廉價成本,包括廉價勞動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還有政策的紅利: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招商引資給外企在稅收、進出口經營權和注冊資本等方面開出了很多優惠政策。
而現在,中國制造的各項成本紅利正在快速消失。
在東南沿海地區,“招工難”成為各企業老板們這些年最焦慮的問題之一。2018年的情況則更加特殊,一方面受到內外經濟形勢影響,部分企業訂單不足,很多工廠年前提前放假,節后推遲開工;另一方面,一些有訂單的企業,卻招不到急需的一線熟練工人。
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都是這樣:“2018年工廠招工,工人的工資漲了又漲!”“工廠月薪過萬招工難‘馬路游擊隊式’招工該升級了”·······中國用工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實在用工成本上升的背后,還有一個壓力是: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愿意到工廠工作了。
在這些制造業企業中,一線熟練工人平均工資并不低,但多數是四五十歲的老工人,因為培養一個熟練工和技術工,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積累,而工廠的工作缺乏上升空間和穩定預期,也阻礙了年輕人進入。
在自行車制造企業廣州千里達集團車間工廠,已經鮮少見到年輕人的身影,廠長高譜祥說:“目前25歲以下的年輕人只占整個工廠的3%左右,基本上都是35歲以上的員工,人工確實難招。”
再看中國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成本,因為利率沒有實現市場化,目前還維持著全球較高的利率水平。
“中小企業很難在銀行借到錢,這也是為什么這些年P2P等民間資本能夠火起來的原因。”有業內人士提出,商業銀行在選擇借貸對象時,往往很難完全按照市場原則把錢貸給有償付能力的企業,而是把錢貸給國企、地方性大企業等有地方政府扶持的企業。
制造業轉型升級:青黃不接
歸結起來,中國制造業當下的處境很尷尬:一方面是來自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步步緊逼,而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跨入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否則一旦在產業結構升級之前先被東南亞國家或者墨西哥奪走了低端制造,那么我們就很有可能落入“世界工廠,沒有工廠”的境地。
有一些專家建議將產業向西部內陸地區轉移,來尋找新的廉價勞動力。“這并不是長久之計,因為西部地區的用工成本隨著產業的發展,遲早還會升高。所以,最新一次產業轉移浪潮是必然會發生的。”另一些人提出了反對意見。
現在的出路大概就只剩下一個:制造業轉型升級。
然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中國在承接低端制造30多年之后,在高科技方面、創新方面的突破還略顯蒼白:比如飛機發動機、醫療器械、機器人、新材料等技術,我們自己的研發和商用轉換還很不成熟,國外對知識產權又保護得密不透風,產業向高端升級還停留在初級階段。
這是兩個世界的較量。
傳統制造業呼喚新的增長動能,智能制造應運而來,光環纏繞的機器人尤為耀眼,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政府、資本充當著“游說者”的角色,不管有沒有實力的企業都打上了“機器人”的標簽。
一些已經無法招架人工問題的制造業企業也絞盡腦汁想著改變,自動化改造是一個出路,但是目前,他們卻很難接受投資回報周期高于2年甚至1年的項目。
“成本還是太高了,風險很大。”中小企業們都心有余而力不足:“用不起機器人,最終還是量的問題,最后,自動化產線就變成一個樣板,客人來的時候參觀一下。”
“不只是我們,還有比我們更大的企業也不愿意投入,沒辦法,整個行業的利潤都很低。”有知情人士吐槽:“一條生產線,要投入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對于我們來說成本太高了,汽車行業一條自動化生產線投入幾千萬甚至上億還說得過去。”
一方面是生產成本壓力增加,招工難;而另一方面,是機器人設備成本還沒有達到企業可以接受的范圍,這種“青黃不接”的情況下,也難免有企業想要撤離。
用得起機器人的企業也有“青黃不接”情況:自動化產線效率未能達到預期,投入后節拍大打折扣;機器人穩定性欠缺,故障導致停產;機器人智能化、柔性化程度不夠,還有未能完美解決的工藝問題等。
有制造業企業負責人表達不滿:“說是海歸團隊,要用人工智能改造產線,連工藝都沒了解過,一問三不知。”
“預期2-3年回本的產線改造,實際做下來,4-5年能回本就燒高香了。再加上使用過程中經常遇到各種小故障,效率甚至還不如人工。”在高工機器人的巡回調研中,康寶電器副總裁陳國祥先生曾向我們吐槽。
盡管如此,他們都清楚地明白,如果還想在中國維持生產,自動化是唯一的出路。“未來實在招不到人了,自動化肯定是要上的。”
2019年是一個坎,但也許是“機器人行業覺醒的一年”,在市場給了我們一記“響亮的耳光”之后,“沒有捷徑可以走,只有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沉淀、開拓、堅持。”這是多數人得到的教訓。
但愿我們可以在穩步中走得更快一點。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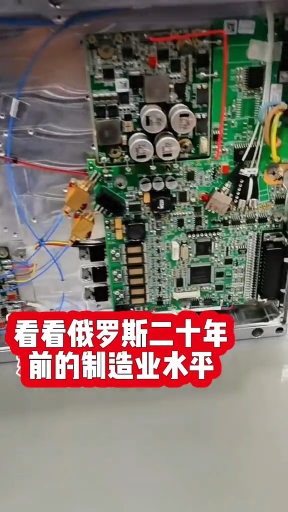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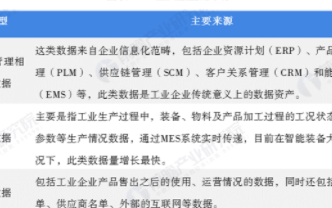










評論